小时候,母亲把我比喻成一钵捧在手里的滚烫的油,怕一个不小心,便摔了!这是母亲在我长大后,形容我小时候的情形。
那时候,母亲怕我在街上变坏,总在我暑假或寒假后,托人将我送往乡下的外婆家。
外婆家很远,离县城有一百多里路,要坐上半天的车。凹凸不平的公路,尘土飞扬,颠簸摇晃。
每天往返的客运车,大概只有两三趟。每次坐车,会看到很多人,禁不住颠簸,翻江倒海的将肚子里的秽物,吐在车窗边,或车内的座位下。
那时,我也算是身材瘦小,面色泛黄,偶尔的不舒服,也会呕吐。更要命的是,车到终点,去外婆家,还要走上五里平路,八里山路。每次走路,心里都在打颤,每次都是硬着头皮走。走路的时候,最贴切的形容,就是一个捱字。捱时间,捱体力,捱坚持。走完了土路,走山路,山路很陡,气喘吁吁,翻过了一座山,又一座山。
最陡的半山间,有一座古旧的板屋,是供路人歇脚的亭子,谓为茶亭。路人可以在此歇脚,喝杯井水,或是凉茶。这是早前,怕赶路太辛苦,一些乡民或先贤捐建的。五里一短亭,十里一长亭,每次路过,我都会在这里歇歇脚,喝点凉茶或井水。
离开茶亭,往外婆家,约摸还有近一半的山路。些许的休息,自然是恢复了不少体力,走路也稍许的快了点。何况有一个带路的长者在前,也不允许我太慢。深山老林的怕天黑,一步一趋的,跟着大人的脚步,翻过最后一道岭,走过一条水渠,沿着一条小路右转,就到了外婆家。
外婆家的小村,四周山峦叠翠,梯田一层层的沿着小路蜿蜒着延伸向远方。
外婆家就在小路边的山下。那时候,外婆的身子骨硬朗,外公在区公所工作,又不常回家,儿女们也一个个长大,去了山外。只有一个读书的小姨留在外婆身边,家里家外的农活,都是外婆撑着。
外婆守着偌大的一幢房子,每天早晨鸡叫起床。第一件事,就是把水缸的水挑满。然后,打扫卫生,生火做饭,煮猪食,我自然是不能闲着的,挑水,打扫屋子卫生的事,就顺理成章的交给我了。好在出门十几米,就有井水,井水边的泉塘,顺便可以看看鱼……
打扫屋子的卫生,就可能要受外婆的训斥了,棕叶做的扫把,扫地并不顺手,外婆家的大厅和灶房,中间隔着一道木坎,泥土紧实的黑色的地面。所谓的客厅和卧室,分列大厅的左右侧,用杉木板铺着,与地面隔空几十公分。那隔空的地下,是用来养鸡鸭的。以进门的厅堂为界,左边养鸡,右边养鸭。每天早上,打开系门,把鸡鸭放了,让它们去野外自由地寻找食物。晚上再用几把稻谷,把它们召呼回家,关入这隔空的几十公分高的空间里。
我是城里人,外婆却不惯着我,除了这些挑水扫地的事,外婆还会让我洗碗,捡拾柴禾,有时还会去田边扯猪草。
割禾和扮禾,是最重要的农活。外婆心疼那掉在地下的谷子,不让我学了!翻红薯藤,我算是学会了的!那是烈日下的夏天,没有一丝的风。为了让红薯长得壮实,外婆带着我,在那红薯地,将那红薯的藤,一些细小的根扯出。然后,像梳女人的辫子般,一根根,梳直理顺,而且不可以偷懒!直到把所有的红薯地整理完……
在外婆家的大部分时间,除了干农活,剩下的时间,都是我一个人,腰间系个装泥鳅的竹篓,去田里捉泥鳅。
那时的乡下,山里人极少走出山里,外面也很少有人进来。哪怕是一片外村的树叶,掉落在本村的地上,他们都能知道。只有逢五逢十赶场,他们中的一些人,才会走出山村,去十里远的公社集市,买几尺布,做几件件衣裳,或是买一些山里不常有的日常用品。
我衣着并不光鲜,走在村里,他们大都认得我,他们知道我是城里人,他们甚至知道我是海婶娘的外孙。(他们称我的外婆海婶娘)他们会很亲切的招呼我:“进屋喝杯茶吧!”“你是碧莲姐家的孩子吧!”“你是老几啊?读几年级了?几时进来的呀?”我一一敷衍的应着,答着。
光着脚,走进了那一丘一丘的梯田里,捉泥鳅!那是我少年在外婆家,最快乐的事了。外婆家方圆几里地的稻田,被我捉了个遍!每次捉的泥鳅都是很少,外婆却一样欢喜。最多的一次,我竟然也捉了半斤!
外婆用柴火将泥鳅在铁锅里煎成半熟,然后剔出泥鳅内不能食用的脏东西,再用细火慢慢用油慢慢的煎,把泥鳅煎得酥脆,喷香。再放入花椒,鲜辣椒等。一碗可以把舌头都吞下的美味出来了,那想想就口内蠕动的美味,令我至今流涎!那都是夏天暑假的时候。
到了冬天,天上飘起了雪花,地下落了一层厚厚的雪。外婆村子里的村民,一般都不出门了。 大部分都猫在家里,烧着柴火或木炭火,围坐在一起取暖,聊家常。饿了,就烤糯米做的糍粑。
过冬的萝卜和白菜入了地窖,取暖和生活的柴禾,在夏天就准备好了。粮食也收了仓,过年的腊肉,挂在樑上。年后走亲访友的糍粑,也都凉干了。
银装素裹的山村,一切都显得那么安静,静得能听到雪落下的声音。
这样的天气里,外婆很少出门。因为寒冷,我也不能去小溪里捉鱼,去稻田里捉泥鳅。偶尔带上我出去串门,要小心地将稻草绑在鞋上防滑。走在沙沙作响的雪地里,脸冻得通红,我却很是喜欢。这样的天气,适合堆雪人,打雪仗。我这样的想着,却没有一个和我一样心思的伙伴。
外婆却是一种另外的心思。要过年了,外公也该放假回家了吧!那在外面工作的几个,会回家过年吗?
我想起了城里的伙伴,想起了那震耳欲聋的爆竹,父母的压岁钱……
稀稀疏疏的爆竹声过后,外婆家的小山村就沉浸在阴历年的喜庆中了,乡里乡亲的拜年,就是一块腊肉,数量不等的糍粑,加上一只板鸭。
最喜庆的闹腾,要算是舞龙的了。舞龙的都是四里八乡的村民,他们每到一家,主人都会用鞭炮迎接,这时候,有学了武术的,就会打上几趟拳,图一个喝彩,赢几个糍粑。舞龙的队伍围着主家的晒谷坪转上一圈,又赶往另一处板屋,主家还是拿出糍粑打发他们,这样的一条龙,连敲锣打鼓的,一起有二十来人。外婆家的山村,一天要来好几条。听说夜里还有草龙,我却是没看到……
多年以后,外婆家的小姨去外地读书了,后来也留在了外地。外公退休不久也走了,外婆一个人守着她的板屋,屋里也不像从前般整洁。外婆老了,老得走路都困难,在城里崽女处住了会,却不习惯,又回到了小山村,这时的小山村,通了水泥路,每日里都有汽车出进,
山外的小洋房,村里也有了。
外婆身体却每况愈下,终于走了。留在离村子两里路远的地方。那地方,和外公隔了一条水泥路,可以终年听到清澈的泉水叮……
作者简介:罗文辉:现年54岁,湖南省新化县人,原湖北郧阳武警支队服役,现在湖南省新化县自然资源局工作。喜欢文学,有诗歌和散文发表于杂志和公众号。

中国记录新闻网所发布资讯欢迎转载、引用,务请注明来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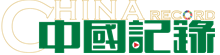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