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记录通讯社(记者:王玉伦 黄庆松)贵州消息:沿着水城河的堤岸慢慢地走。这河,原是认得旧时容颜的,如今被整治得这样齐整、这样温婉,倒像是位疏于问候的老友,忽然换了一身光鲜的衣裳,教人有些惊喜的陌生了。水是静静的,绿莹莹的,像一块硕大而凉的玻璃,将天空的蓝、云朵的白、以及两岸那一片煌煌的金黄,都毫不吝惜地收纳了进去。风是有的,却并不凛冽,只是悠悠地、一阵一阵地拂过来,像个好奇的孩子,用软软的手指,不停地翻动着树梢上那本用金叶装订成的、厚厚的秋之书。于是,那叶子便“沙沙”地响,那光影便明明灭灭地晃。


抬起头,看那樱花树的枝桠,真是画家笔下的好线条。它们并不杂乱地虬结,而是舒舒展展地、带着一种从容的自信,向着清寂的天空伸张开去。夏天里那一场轰轰烈烈的、粉色的花事早已成了过往,此刻的繁华,是叶子们的。那叶子,并非是那种单一的、纯粹的黄。有的边缘还残留着一丝半缕的酡红,像是少女贪杯后未褪的腮晕;有的通体是明亮的金黄,像刚从熔炉里蘸出的金箔,薄而亮;有的却已呈出焦糖的褐色,沉甸甸的,仿佛承载了太多阳光的记忆。阳光呢,这时候便成了最高明的魔术师。它从那枝枝叶叶的缝隙里,小心翼翼地探下身子,那光便不是一整片的了,被剪得碎碎的,成了无数跃动着的、圆圆的光斑,洒在赭红色的步道上,洒在人们的肩头、发梢,也洒在底下那脉幽幽的流水上。水波受了这光的撩拨,便将它揉成更碎的金片银片,懒洋洋地漾开去,教人看得有些出神。

树下是人。三三两两的,多是些悠闲的市民。有年轻的母女,小女孩穿着鲜红的毛衣,在落叶铺成的毡子上蹦跳着,每踩一下,便发出一声清脆的“咔嚓”声响,她于是快活地笑起来,那笑声也像带着颜色,是透明的、亮晶晶的。她的母亲则举着手机,弯着腰,极耐心地追随着孩子的身影;那小小的屏幕里,不知装进了多少帧这秋日限定的、会动的图画。也有白发相偎的老伴,并肩坐在河边的长椅上,并不说什么话,只是静静地望着这流水,这黄叶,这熙熙而过的路人。他们的膝上,或许已落了一两片叶子,他们也并不拂去,任由那金黄点缀着他们素色的衣裳。这光景,是静的,却又不是全然的静;那静里,有一种饱饱满满的、岁月沉淀下来的安详与温和。这比起从前,确是不同了。我恍惚记得,这地方早年似乎并非如此光景,河道或有些芜杂,景致也带着些乡野的、不修边幅的朴拙。而今这一番精心的梳妆,竟真将一片荒疏,点化成了人人可亲、可游、可憩的乐园了。

正想着,一阵稍大些的风来了。这回,它不是翻书,倒像是要将整本书都摇散了。满树的叶子都颤动起来,那簌簌的声音,便汇成了一曲宏大的、却又极轻柔的合唱。先是几片,继而便是纷纷的了,那叶子,竟真的开始落了。它们并不径直坠落,而是打着旋儿,左一下,右一下,飘飘摇摇,恋恋不舍,真如一只只倦了的、金色的蝴蝶。它们在空中舞着生命里最后一支,也是最自由的一支舞。有的落入了河水,便成了一叶小小的舟,载着阳光,悠悠地远航去了;有的落在了人的肩上,便像一枚精致的徽章,别在了季节的衣襟上;更多的,是安然地、厚厚地铺了一地,将一条小径都染成了辉煌的金色。我站在这漫天飞舞的叶雨之中,几乎要痴了。这无休无止的、静默的飘落,比任何喧哗的典礼都更庄严,更动人心魄。它不叫人悲伤,只叫人感到一种圆满的、自然的代谢。

我于是恍然,六盘水这座城,昔日总被人与“煤海”、“凉都”的硬朗名号相连,骨子里似乎总带着些工业时代的、钢铁的冷峻。然而此刻,这柔和的、遍地的金黄,这水边的静谧与笑语,不正是它另一副动人的心肠么?它不再仅仅是一座因资源而闻名的城,更是一座因生活而可爱的城了。这一河的金叶,便是它最温柔的诗行,写给每一个居住于此、或偶然到访的读者听。这景致的打造,看似是栽了几行树,治了一道水,其深处,却是一种将自然请回人间,将诗意融入日常的苦心。市民们那脸上闲适的笑意,那不必远行便能“赶赴”的“季节之约”,便是对这苦心最好的回报了。

天色渐渐地向晚了。西斜的太阳,光线变得愈发绵长而醇厚,像稀薄的蜜糖,涂在万物之上。那一片金黄,在夕晖里愈发显得浓郁,几乎要燃烧起来。游人渐渐散了,周遭复归于宁静。只有那叶子,还在不紧不慢地落着。我踏着来时的路回去,脚下是酥脆的声响。回头望,水城河两岸,依旧是那一片无声燃烧着的、静默的火焰。这一场盛大的凋零,竟比花开更令人心折。冬风年年吹,红叶岁岁黄,这一场与金黄的约会,想来明年,后年,还会在这水城河畔,静静地等着我呢。

中国记录新闻网所发布资讯欢迎转载、引用,务请注明来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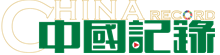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评论